胡司令走马上任当医官的那天,天上正飘飘洒洒地下雨。伙食团破例添了两个荤菜,记得一个是苦瓜炒腊肠,另一个是火焙鱼炒红辣椒。不料满饭堂人正吃到热闹处,那胡司令却毫不客气地当着一桌人放了个响屁,“呜呜”地山响,害得一屋人笑不是,哭不是。一下子便扫去了许多人的兴致。及到后来胡司令削职为民,当了伙头军掌勺子,我便在心中暗想,这极可能与那个不吉利的响屁有关,就好比李自成打进北京城,到了金銮殿前正要一箭定乾坤,却偏偏地射离了的,而后便败离京城到江南的某处名山入空门为僧一般。
其实,胡司令上任后的一长段时间里,我们都是亲亲热热地叫他“胡指导员”的。就象当兵的叫连长那样,只差少了个“立正”、“稍息”。想必一是因为他这人的身材长得有些酷似现代革命京剧《沙家浜》中的胡传魁,壮壮实实,一脸横肉,且性情脾气也有些类似;二是因为他在这间小小的区医院干指导员的营生没干上几个月光景,就被罢官到伙房当了伙夫,那伙夫逢到饭熟菜香便敲响檐边吊着的一块生铁,发出“当当”的响声,通知医院里的男男女女去食堂进餐,大有钟声响,人马至的司令效应。于是也就有一天记不清是谁叫了他一声“胡司令”,这一叫便相袭了十来年光景。
那时,我刚参加工作不久,在这间医院里当了个司药员。医院有两间药房,一间是西药房,在东端的一间小房子里,墙上掏个小门洞,算是窗口。司药的是个老太婆,从市立医院下放来的,很有些本事,会配制清凉油、十滴水一类的东西,那年月这类药品也是奇缺的,所以到了夏天,那小窗口前便经常挤满着叫叫嚷嚷的人们。在西端的一间大房子里,有着一排四个很大的赭红色的药柜,上面密密麻麻排着许多的抽屉。最难得的是窗前有一架葡萄,一到八、九月间,先是碧绿的,后是紫绛的葡萄粒儿便将香味儿频频送至屋来,馋时,我便可得天独厚地在屋里攀着窗棂去摘下一串尝尝。其实,那些年,市场上的计划经济秩序也还是很井然的,不比现今,什么都由倒爷插手。比如红枣、龙眼这类可作药用的东西,市面上虽说是很难寻到的,国家却也不知从哪里弄来一点,时不时给些。所以,我那间中药房便不时有人来求着开点后门。有一晚,胡司令到我宿舍来坐,我刚倒上杯水,还没来得及递给他,他便“呡”了一声说:“去给我搞两斤红枣。”
我一听,便想笑。
那时,胡司令已经没当指导员了,伙夫一个,比我还矮差不多半粒米。他见我不作声,便也闷闷地坐在我床沿上,时不时抬起头望着天花板上的一只大蜘蛛织网。还不时地递给我一支“丰收”烟。记得那烟是一角三分一包,烟盒上一个农妇怀抱一束麦穗。别看那一角三分钱不多,那时月鸡蛋5分钱一个,一天的伙食费也不过三角多钱,还包吃热饭热菜,包供热茶热水,挺够意思的。我那时月工资29元5毛。有一回,区上开会,县上来的一个工作组长说:“如今年轻人享福哩,20来岁,每月几十块工资,吃饱饭还有余钱。我那时当长工,年头累到年尾也只有12石谷哩。”那天,胡司令不知为何清白起来,不象平日里那般糊里糊涂。我正坐在他旁边,见他折着指头在算什么,一会,他用手肘碰了碰我,说:“你好多钱一月?”
“29元5。”我稍稍迟疑,道。
“当得长工么?”
这账,说良心话,我会算。一月下来,无论如何节省,除了吃饭、买牙膏、牙刷、肥皂什么的,能省下15元了不得了吧?那年月,稻谷30来块一百斤,15元钱刚好买上50斤谷。当长工不是每月一石谷么?一石有130来斤,一月强出80斤谷哩。不过,我没作声,只是“嘿嘿”地奸笑了一声。
记得胡司令叹了一声。我侧头望望,便见他双眉紧锁,眉心间聚起三道竖纹。
不久,便传说胡司令那晚和县里工作组的干部理论上了,他硬说青工当不了先些年的长工。这事我倒是相信有几分。胡司令就这样去伙房当了伙夫。我暗自庆幸菩萨老爷坐得高,那晚没多嘴多舌惹是非,落得个平安无事地继续当那小小的司药员。
那晚,胡司令就这样坐着,十点多了,我想睡,便虚张声势地打了几个呵欠,记得是三个还是四个,那意思明摆着是催胡司令快走。胡司令心里也是清白人,这我知道。他便说:“你莫厉害,就开那么半斤、一斤的后门则行。”我知道缠不过他,就问:“要红枣做甚?”
“做单方呗,人家托的。”他说。
我早就听人说,他有个相好的,是个寡妇。想侃侃他,又想,他毕竟是长我一辈的人了。旁的事玩玩可以,这类事可容易伤人面子。便说:“你明日来吧,中午人少,免得让人见了。”这才终于打发走他。
从这以后,胡司令也和我有了些交情。那时食堂开饭,凭饭菜票一人三两饭,一小碗菜。菜大都是蔬菜一类,萝卜切丝是小菜,切丁炒辣椒大蒜是荤菜。肉是少得吃到,偶尔一次,也是白白的几片,或炒白菜头,或炒苦瓜片。这胡司令实在算不上一个合格的伙夫,做出的饭菜寡淡无味且不说,最可怕的是那卫生状况糟得令人发毛。我们曾问过胡司令,这肉里为何不淋上几滴酱油?问这话时,他正在锅边炒菜,便抬头瞪了瞪我们,又侧头擤了擤差不多流到唇边的鼻涕,用手掌左右二下抹抹,道:“一角三一餐,还要放酱油?你娘又莫不是我野婆子!”那时,我们自然有些恨他,却又无可奈何。讲多了,保管连着几天碗里的青菜都只小半碗,甚至还有可能从白菜里吃出一截白晃晃的蛔虫来。于是,我们也就只好忍了,很少和他理论。
第二天中午,胡司令果然到药房找我。我也不再哆嗦,趁外面无人,称好半斤枣子包了给他。他一走,我去关药柜屉子,见里面红枣已不见了几颗,我明白,趁我去柜台上包枣子背朝着他时,他偷了枣子。我“砰”地一声关门去追他,走了十多步,又想何必呢?便转身回到药房,拿笔在一张旧报纸上一连写了十几句“日死胡司令的娘!”
从此我更看不起他。不过,胡司令却蛮瞧得起我,往后好长一段时间,我的菜碗里总要丰盛点。碰上吃肉,明摆着碗里的肉要多好几片的。我也不讲什么客气,端着碗边走边夹着肉往嘴里塞,及到饭桌上,碗里便只剩几块萝卜或菜头一类的东西,摆在那里让人慢慢瞧见。如此许久许久一段时间,也未能让旁人觉察出我和胡司令之间的任何一线蛛丝马迹破绽勾当来。
吟诗也是长寿药 上一篇 | 下一篇 失过身的和又陷入情网的秋莲
- 醉菊楼笔记(上卷)寒江集2011-06-28
- 《肝病健康全书》——杨旭教授专著2009-08-26
- 醉菊楼笔记(下卷)清风集2011-05-03
- 张其成讲读《黄帝内经》:养生大道2009-06-30
- 醉菊楼笔记(中卷)朗月集2011-04-27
- 老年食养食疗2009-07-27
- 教养可以这么浪漫2009-07-27
- 小方治大病(家庭中医药养生精华录2)2009-07-27
- 好身体是走出来的2009-07-27
- 《不生病的15个饮食习惯》2010-12-22
-
医生姓名:刘伏友
所在科室:肾内科
工作医院: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专业职称:主任医师
擅长疾病: 腹膜透析、各类肾病、慢性肾功能衰竭、尿毒症、血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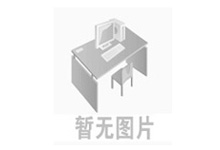


 湘公网安备 43010502000198号
湘公网安备 43010502000198号